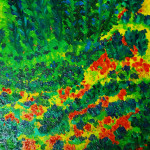小時候,我常和外婆上教堂。在彌撒正式開始前,就會有很多教友坐在位置上,有的默默的祈禱著,有的則細心讀著聖經。在教堂後方通常會有兩個小亭子,左右一邊各一個,我總是看著有人排隊,一個接一個進去那個小亭子的側面。過了一會之後出來,再換一個人進去。只知道神父坐在那個小亭子裡,那些人是排隊進去和神父說話。
長大一點之後,才知道那是個告解亭。教友們會走進那個小亭子側面,隔著很小一扇窗戶,向神父告解,訴說著自己近日裡的麻煩,困擾,或是自己行為出格的事,或是對人產生的厭惡和說過些傷人的語言,他們認為自己這些行為,不符合神的旨意或約束,所以請求神父的聆聽,讓上帝原諒自己的罪行。當然,有的時候,他們只是去說說自己無處可說的困境,通常神父只是聆聽,然後和告解的人一同祈禱或唸段經文,但告解的教友就此放下了心中的負擔,走出小亭子,整個人煥然一新,充滿希望如獲新生。
有宗教信仰的人,或許會把自己的秘密和痛苦,交託給他們所信仰的神。沒有宗教信仰的人,也許或透過心理醫生,或是心理諮商師,說說自己的煩惱,或是尋求解決之道。但大部份的人,會和自己的好友分享,互相倒倒內心的垃圾,一切就是會了讓不好的情緒有個出口,抒發完之後,一切歸於平靜,又可以充滿正能量的看待自己,重新回歸生活的軌道裡,繼續向前。
還有大部份的比較安靜,比較注重隱私的人,他們會寫日記。他們不想把自己的事大張旗鼓的到處去說,不管是開心的,悲傷的,痛苦的,憤怒的,怨恨的,他們只想說給自己的日記聽,他們以這樣的方式記錄自己的生活情緒。不管當下的心情是如何,他們可以以各種字眼來形容,甚至用自己平日最不可能的粗話,來表態自己內心的憤恨。當下寫完,那些詞句就如同打開的自來水,嘩啦啦的從心底流掉,再也不存在了。因為他們已經透過這樣的方式,抒 發掉積壓在內心的不快,或是把那些甜蜜全部封印,因為生活還是要繼續往前。
發掉積壓在內心的不快,或是把那些甜蜜全部封印,因為生活還是要繼續往前。
應該很多人都是如此,走出告解亭覺得得到救贖,走出心理醫生的診間,覺得自己內心少了負擔,和姐妹或哥兒們吐完苦水之後,覺得整個人精神了,寫完日記,覺得世界遼闊了。
所以這些私密的情緒,我們也都只讓特定的對象知道。因為那些都是潘朵拉盒子裡的禁忌,不能讓它存留在人世間過久,因為那會腐蝕我們原本善良的心。因為那里面有很多負面的情緒,必須從我們身體裡釋放出來,因此我們要找到可以傾聽或是保守秘密的專門人仕,他們不會被我們的負面情緒影響,也能夠聽完就算了,不會到處去宣揚。就是基於這個原因,日記是很多人訴說秘密及抒發的最方便的方式,隨手隨處隨心情可以好好的記錄抒發,因為不會傷害任何人,只藏在日記裡。
有個小小的實驗,分別找了兩對父母,把一本日記放在他們面前,告訴他們這本日記是他們孩子的日記,然後讓這兩對父母決定要不要看孩子的日記。
A組父母倆人很一致的把日記退還給實驗人員,並請他們將日記還給自己的孩子。父親表示要瞭解自己的孩子不需要透過孩子的日記,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多陪伴自己的孩子。多尊重孩子,並且信任孩子,孩子自然會和父母分享自己世界。若是不想分享的事,也讓他們自己消化,這也是成長的一部份。而母親表示人都有情緒化的時候,日記中可能記載了孩子的一些秘密,而人都是有秘密的,既然是秘密就更不應該去偷窺他人的秘密。
B組父母討論得很激烈,父親覺得不該看小孩日記,但是母親認為必須要看,才能知道小孩私下的生活,這樣有助於瞭解自己的小孩。父親認為日記記錄的心情是短暫的片刻與不理智的情緒,不足以代表孩子真正的一切。母親不顧反對打開日記,結果發現孩子日記中常常出現批評媽媽的段落,譬如說多管閒事,不尊重小孩,干涉太多等等,以及不堪的字眼。媽媽當場崩潰,大鬧要回去和小孩理論。太太說從此再也不願信任小孩,引來先生的不滿,表示偷看他人日記是侵犯他人隱私,對教育孩子來說,太太剛剛已經做了最錯誤的示範。
對很多人來說,日記就是潘朵拉的盒子,裡面裝滿貪婪,虛無,嫉妒,猜忌,毀謗,痛苦和快樂和希望。人,可能都有偷窺欲,或是想探究別人秘密的好奇心。然而偷窺就如同要打開潘朵拉的盒子一般,將會感受到各種不堪的情緒,和龐大負能量的洗禮。以及很有可能自己就是負能量里的惡魔一角。
所以想要偷窺或是打探別人深埋秘密的人,真的該問問自己,扛不扛得住那樣的負能量襲擊?被貪婪,虛無,嫉妒,猜忌,毀謗,痛苦冲击之后,是不是就此也一身是傷,真的可以承受這種打擊嗎?或者問問自己的道德感,是不是自己應該把自己這樣的念頭好好的深埋起來,別再任他誘惑自己去打開那個潘朵拉的盒子,這才是保護自己最好的方式,非禮勿視,這道理孔老夫子老早就告訴我們了,不是嘛?